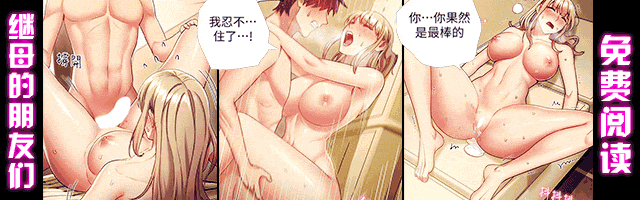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也是哈,这样的人家都是暗地里下帖子请您接诊,这么招呼都不打直接来的,头回见。”扶风囫囵吞下口里的绿豆冰汤去迎。
看见那檀木雕花儿硕大跟个小房子似的宝鼎墨紫绸八匹骏马拉的鎏金八角宝盖车震惊在原地。
随行的二十多位侍从全都穿着银白软猬甲,手持着红缨枪。
另有仆人掀开玉珠车帘,捧起飘飘欲仙的香云纱,两个发髻精致,戴着金玉珠花儿,身着鹅黄对襟夏衫葱绿绸裙的秀丽侍奴下马,娇声滴脆的道:“回禀王嫡君殿下、翁主殿下、自在堂到了,请主子下车。”
侍奴搬来脚踏,一个身着素白锦裙外罩水蓝宫样祥云纹半臂雁粼绸的十四五岁小哥儿敏捷英气如雪色鸿鸟般走下马车。那小哥儿又回身扶着另一个穿着淡紫长裙金纱披帛的贵族正君夫郎打扮的、有些看不出年纪、却非常清雅如菊梅带几分病弱之态的小哥儿下了车,口中不住叮嘱:“阿姆,小心,慢慢的。”
“大热的天儿,去寺庙上香后再来瞧病也是难为阿姆了,只是父王再三叮嘱要素素照顾好阿姆,带阿姆来的。”段尺素对江阳王嫡君柔声道。
江阳王嫡君,给段尺素擦了擦鬓边的汗,正一正自己独生小哥儿发髻上的簪子:“阿姆知道你的心。”
“阿姆我们进去吧……”
扶风倒吸气,忙跑回堂里,见楚江不知去哪儿了,赶快去后堂寻,见楚江在切草药忙拽他:“师父,是昌乐翁主段尺素和他阿姆江阳王嫡君来咱们医馆了!”
“你说啥?”楚江抹去额头的汗,站起把掖在腰际的长衫下摆放下来,袖口还胡乱的挽着,头上还沾着草药碎渣,忙边用长衫下摆擦手边出去迎。
“贵客临门,有失远迎,见过江阳王嫡君殿下,见过昌乐翁主殿下。”楚江和扶风忙行礼。
段尺素在他还没弯腰下跪时一把握住手肘,微笑:“楚先生何必客气?我和阿姆今日也是择日撞日,贸然来这需要拜帖的神医仙府,只是不知一向多出诊内宫中,甚少坐堂只卖成药丹丸的楚神医肯不肯给我们江阳王府一个薄面,坐堂为我阿姆看诊呢?”
楚江表面倒也从容,心中暗暗咂舌段尺素的交际手段:“翁主实在是客气,这边请——”
本想在正堂看诊,但正堂被他和扶风弄的乱糟糟,摸着喉结上的伤口,心说,段尺素明摆着有交好的意思,刚好能平衡镇北王金玉楼那边的压力,不如试着君子之交,因而把他们姆子往后堂的正房大厅上引。
“自在堂前边我正在收拾,就请委屈王嫡君和翁主在我家这粗陋正厅接诊吧。”
段尺素环顾正厅一圈儿,正对大门是梨花木大罗汉榻铺着玄翠竹纹密布垫儿,榻上放着雕荷花蜻蜓的蓝翡翠炕屏,两侧分别立着黑檀木官帽椅中间插高几茉莉鲜花,左右耳房都没有用石墙隔断而是用多宝阁和书柜,满满当当的全都是各种书籍墨砚瓷器,落地的纱幔都是淡淡的水墨字画儿秋黄渐白间水纱,收拾的大方静谧,简单而不失雅致古拙,可见主人的良好品味。
然而只淡淡一瞧,段尺素就能看得出屋内的许多不起眼儿的摆设价值加一起少说万金,心里不由觉得奇怪。
楚江让他们姆子坐在正位,他看着段尺素并没有坐下,而是搀扶着王嫡君坐上去,并挥退了拿着靠垫茶水等备物的侍奴家丁。
扶风机灵,搬来一只瓷绣墩儿让段尺素在江阳王嫡君跟前坐。
“赵伯,你去库里取些冰来,扶风你去叫碧桃把你师姆收着的峨眉翠沏两杯来。”
“是,师父。”
脉枕已经设好,江阳王嫡君林露嗔优雅的褪下金玉琥珀几只手镯,把瓷白的一截手腕放上去,立即有侍奴取出薄如蝉翼的纱帕覆盖在那上面。
楚江对此司空见惯了,哪怕是悬丝诊脉也难不倒他,把脉一会儿,望了望林露嗔的面庞气色:“失礼,还请王嫡君殿下张嘴露出舌来。”
“王嫡君殿下先天有哮症,索性并不严重,身子康健暂无大碍,只是忧思多则伤肝,怒则伤心脾,还请嫡君素日里不要劳心太甚。”
林露嗔捂着心口,叹气,忧愁极了,拉了段尺素坐在身边:“嗳,果真是神医,我不说,便能知道我身子,更知道我的心思,我这颗心可不就是分成了两半儿,一半儿挂心你,一半挂心你父王,何尝有过半刻得闲儿。”
“阿姆……”段尺素轻轻的为他阿姆把碎发掖到耳后。
赵伯和虞叔搬来了一缸的冰块摆在客厅中央,红叶端着茶水点心来了,几人退下,留扶风站在楚江身边。
“嫡君不防回去念诵清心诀,我这的配方药膳——解忧甜汤,也是不错的,如果要根除哮症,我这里也有一味良药秘方。”楚江笔走龙蛇,很快下了药方子。
段尺素却出声:“楚先生,除此之外,我们还想看生育之症。”
林露嗔脸一红,轻轻去捂儿子的嘴:“未出嫁的哥儿,混说些什么?你个小傻子,身子一直好好儿的,让旁人听了去还以为你怎么了!”
又转头
窘迫艰涩:“我十六岁嫁入王府,三年后才生了素哥儿,伤了身子,再无所出,如今年岁已至三十又四,王府中也有几房侧君小君,怎奈都不争气,江阳王府膝下空虚,是我身为王府嫡正君的失责失德。”
其实,令林露嗔更忧虑的是宫里又要给他夫君塞人,王公贵族谁家不是三妻四妾,他身为男妻有何忍不得的,只是怕招进来探子不能给夫君分忧,更怕后来不端者有孕,动摇江阳王府之根本,让他夫君为国征战之余回府也不得开颜。
楚江看他们姆子俩都开始脸红,不免好笑,脸上却一本正经:“也是人之常情,所谓解疾不忌医,王嫡君和翁主不要羞于开口,反而会延误治疗。”
“是我们浅薄了,还请先生看脉。”
楚江眼睛转了几转,邪门儿,这王嫡君的身子除了弱了点,生育能力没有问题啊。
难道是他诊脉有误?再厉害的能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楚江招来扶风,耳语:“你切脉看看,再与我悄悄说,为师考考你。”
扶风依言去做,诊了半刻钟,来楚江耳边嘀咕几句:“没有毛病啊,就是体质弱点儿,师父你看出啥来了不好说?”
“扶风你去药堂里看看,另外关上门儿。”
扶风立刻去了。
待屋里人只剩下楚江和他们姆子三人后,楚江开门见山。
“嫡君身体无恙,不知江阳王殿下身子可曾有过什么旧疾或是紧要部位呃……受过重创。”楚江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
段尺素与林露嗔面面相觑,明白了他的意思,脸都更红了。
气氛更加尴尬,楚江不得不说:“想必你们在江阳府封地的时候也看过无数名医名士了,无所获,要不然也不会找到楚某头上,所以我就直言不讳了,王嫡君的身子无恙,还能诞下翁主,那么之后十余年无所出,府里的其他如夫人也没有生育,我建议,让王爷来我这儿瞧瞧,病疾不忌医,我会保守秘密,绝不泄露半分。”
段尺素终于张口:“我听叔父说我刚满三岁时,父王剿灭三江水匪时,父王与贼首激战,那贼首的部下匿藏在水中,暗算了父王,父王的左腹中过一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