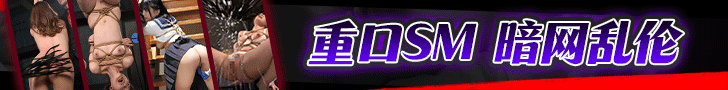池渊扶着墙慢慢的走,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弓起的脊背表达了某些状况。
让行军多年的人弯腰行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此时却没有什么不和谐,好像他本该如此。
池渊艰难的回到了呦鸣院,刚要褪下衣服爬上床,却看到了桌子上摆着的一盘月团。
池渊愣住了,耳朵里不断折磨着他的嗡鸣声停止了,世界奇迹般地安静了下来。
池渊慢慢的走了过去,伸出了手。
他捧着月团,坐在了门槛上,看着那轮满月,低头小小的咬了一口。
胃里这时才觉出饿,他实在是没什么力气了,手心一抖就不慎掉在了地上,历荣走进院子的时候,正看见他从地上把月团捡起来,拍了拍灰,又放进了嘴里。
历荣脚步凝滞了一瞬,没太在意道“跟我走,殿下要用你。”
池渊的眸子闪了闪,又低头咬了一口月团,芋泥的内馅塞了满口,他舔了舔嘴唇道“今日……我不太舒服。”
历荣听见这句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上前抬脚就要踹,池渊身体往后缩了缩,下意识的举起了双臂挡在身前。
历荣收回脚,眉心拧了起来,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人,两人从前不是没有切磋过,他十次能打赢他一次都算池渊放水,他踢过去,池渊若想躲,再怎么样也不会愚蠢到伸出双臂格挡。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没习过武的普通人才会有的姿态。
“你……怎么回事?”
池渊咳了两声,叹了口气,“如你所见,历大人,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所以你要打便打吧,我没力气还手,但是今日真的服侍不了殿下,您告诉他我不舒服,想来殿下不会强求的。”
他想了想,突然又用嘲讽的口吻说了一句,“别的侍奴……也总有来月事挂不了牌子的时候吧,你就当我是个姑娘。”
历荣被噎的心口发闷,他把剑拔出来捅进池渊手里,“我不相信,你拿着它,再跟我打一场!”
池渊握起他的剑,叹了口气,慢慢的举了起来,然后整个剑身就开始抖,片刻就摔到了地上。
历荣自然能看得出来他是装腔作势还是真的拿不起,池渊缓缓的站起身,明明在笑着,历荣却觉得他根本不想笑。
历荣捡起剑,看了他几眼,转身便走,刚要踏出去,又回过身道“殿下没有传召,是我骗你。”
池渊眼中染了惊诧之意,历荣不会说谎,那么为何要让他去。
他连忙追了上去,又被身上的痛楚扯的踉跄了两步。
“慎平……”池渊喊住了他,历荣回眸皱了皱眉,池渊哑了哑声,跪伏于地,“奴失言。”
“池渊,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你这副样子。”
池渊不解的抬起头,“什么?”
“十年前,你起初唤我慎平,我不准你叫,是因为我告知了你我的字,你却没有与我互通,我以为你刻意轻慢,后来我才知道你没有取字。”
池渊点了点头,“你当时不是已经和我说明白了吗,还…呵…还难得的给我赔了礼,说你脾气不好,让我担待。”
“可后来我军衔高于你,你便不叫我慎平了,即便往后几年你青云直上,即便我们同侍于殿下身侧,日日相见,你仍不肯直呼我的名字。”
池渊愣了愣,笑的苦涩,“只是……只是一个称呼而已,是慎平还是历大人,又有何区别,你竟因为这个和我别扭这么多年。”
池渊慢慢的爬起来,长叹了口气,“我出身卑贱,为人不齿,有日听人议论,说你自降身份,与我称兄道弟,实在是愚蠢,我如何敢再叫。”
历荣的瞳孔缩了缩,他半晌才道,“我没有想过这个原因,我只当你生性凉薄,是无心之人。”
“好一个无心之人……”池渊单薄的衣衫被风吹的鼓了起来,他抬手按下,静静的看着历荣,“我此心何鉴,并不重要,告诉我,殿下怎么了?”
历荣咬了咬牙,“你让我怎么再信你。”
“你不必信我,你只要告诉我,他现在好还是不好。”
历荣静默了片刻,抬起头道“他不好。”
寝宫外层层把守,槐夏看见历荣回来,红着眼抬起了头,她指向床榻,历荣快步走过去,看见周涉川的脸色苍白到极致,紧闭着双眼,几息便要难以抑制的闷哼的一声。
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周涉川微微动了动眉心,“都出去…咳…咳咳…槐夏留下就行。”
历荣向槐夏使了个眼神,槐夏看着他身后的人,默默的起身了,暮岁躺在梁上往下看了一眼,又把眼睛闭上了。
周涉川伸手抓住了床幔,月色寒凉,将皓腕衬得更莹白,只是青筋暴起,徒增了几分厉色。
他哑着嗓子问,“如果我不再服药……可能压制得回去?”
池渊在一旁将帕子浸湿了,费力的拧干,凑到他身旁一点点的擦净了脸颊上的细汗。
“槐夏?
”
周涉川费力的睁开眼睛,只看到了一道重叠的虚影,再定睛一看,偏头躲开,冷了冷声“你来做什么。”
池渊起身又将帕子浸到了热水里,几次反复,重新回到榻前,掀开了被子,将衣裤褪下,果然看到了一片乌青,他抬手将帕子覆了上去,“殿下怎么还是这样,不让人揉开,又要疼上数日。”
“你以什么样的身份同本王说话。”
“旧友。”
“呵。”周涉川仰头笑了一声,撑着身体从床榻上坐起,“出去。”
池渊低了低头,缓缓的褪下了衣服,露出了苍白的皮肤。
他双唇上也没有血色,一双眼睛里满是担忧之色,“我说错了,殿下别赶我。”
周涉川咬了咬牙,抬手扇了过去,“出去!”池渊被打的偏过了头,然后又静静的转了回来。
他舔了舔嘴角,突然勾唇一笑,爬上了床榻,从周涉川的脚底爬进了被里,周涉川呼吸一窒,眼睁睁的看着池渊从他身侧露出了头来。
周涉川的眸色越来越暗,“说错了?那你说对一句给本王听听。”
“奴承蒙殿下青眼,却狼心狗肺,以怨报德,如今自然不能再称一句旧友,奴是特地前来,为殿下纾解的。”
“本王不缺侍奴。”
“是,您不缺侍奴,但您待下人一向宽和,难以尽兴,而奴是叛主之人,配不上殿下怜惜,殿下不必拿我当人看,可随意打罚。”
随意打罚……周涉川捏开了他的嘴,盯着他口腔深处少了的两颗臼齿,“本王未必比肖封仁慈,你不要自寻死路。”
池渊垂眸,“奴若能赎罪,死在殿下手里,也算解脱。”
周涉川抬手又是一掌,直接把他的脸打的猩红一片,口中似是嘲弄似是愤怒“你倒是乖觉。”
“滚下去。”
池渊慢慢的爬下了床,双膝往寒凉的地上一磕又是一哆嗦,眼见周涉川起身,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当他的手摸到了殿宇角落里供着的碎雪鞭时,恨不得当即逃走。
那可是碎雪鞭!是比洛朝的荆棘剑要狠历数倍的东西,池渊从前最不喜于洛朝对战,只因捱上几下荆棘剑,就要修养很久,如果荆棘剑是让人烦心,碎雪鞭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程度了。
被这东西打上一下,皮肉不见破,却瞬间可把深处的血肉碾碎,只能将表层的皮划开,生生的把腐肉剜去,可谓痛不欲生,因太过暴虐,除了对战洛朝时,周涉川已经不常用了。
池渊不知道周涉川是怎么想的,他下意识的就开始算计自己能捱多少下。
捱一下,今晚就侍奉不成了,捱两下,他怕是要当即昏死过去,捱上个五下,他这条命就得折上半条。
不过打他应该不用带上内力吧,如果是这样,打个下,他应该还能撑的住。
池渊深吸了一口气,一言不发的等着,周涉川取过了碎雪,踱步而来,然后鞭梢就慢慢的划过了池渊的背脊,让他炸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殿……殿下…”
“嘘。”
鞭锋凌厉,劈头而下,池渊瞬时从跪伏变为了匍匐,他咬紧了牙关,却是半天都爬不起来。
虽然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但他没有想到,周涉川真的用这条杀敌的武器来责他。
何至于此。
“殿下……咳咳…今日秋节,不宜杀生。”
周涉川收起鞭,拿鞭柄抬起了他的脸,缓缓道“你不是不让本王拿你当人吗,本王现下心中躁郁难平,需泄愤,你有疑异?”
池渊现下对痛觉有些麻木了,竟不觉得无法忍受,他喘了几下微微平复,眼睛红了红,“好疼。”
“别撒娇,本王不吃这一套。”
“您吃的……”池渊小声道。
“啧。”
周涉川将碎雪扔开,躺回了床上,“今天是秋节,回去早点睡吧。”
“殿下的脸色比刚才好了些,难道是因为奴在此吗。”
“别自作多情,再不走,就让暮岁把你扔出去。”
池渊掀开被就钻了进去,侧身把周涉川抱住了,“你……”
“殿下……好冷…让我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