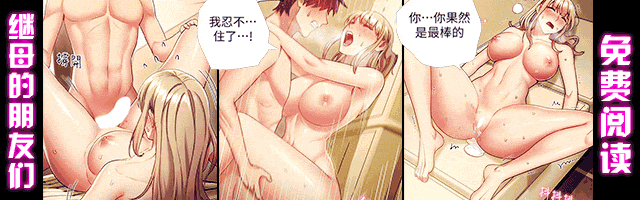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那我呢?”
“你一定会活得很长寿很长寿,三代——不,四代同堂。”
“那么久?”
“当然了,你保护过那么多人,他们都会在天上庇佑祝福你的,我也会。”
火焰灼热,轰轰如风,说着何年何月何时何地什么人曾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话。
似真似幻,似记忆,似轮回。
时间重合般的记忆片段复苏如一记重重闷棍,强烈的昏暗轰然侵占了他的视野,爆炸般骇人的火焰灿烂过橘子般的霞光,在俞骁目眦尽裂的眼眸中金蛇般狂舞,眼底却是黢黑如潭,渗不进光。
俞骁看不见了,在生死攸关的一刻雪上加霜般地,陷入了不知何时会复苏的短暂性失明。
可仅有的一根绳索已经扥到了笔直,没有片刻停顿与犹豫地,他手腕上挽起几圈的铁链稀里哗啦地被松开。
“回来——!”
他火光跃动的双眼里炸开鲜红血丝,人皮面具的边缘已隐隐崩裂开蛛丝般细细的纹路,一道潮湿的水渍从他欲裂的眼眦坠落,血气扑鼻。
回来,还有很多话没跟你说。
他想说,我一开始就认出你来了。
他想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想说,对不起,重逢是那么的糟糕而不合时宜,可我还是有一丝侥幸的窃喜——我很想你。
他想说,你是不是很疼很难受,而不是问他为什么哭,他明明知道原因。
他想说,对不起没有保护好你,而不是侮辱似的来一句你是不是想做欲望的奴隶,他明明知道那样会伤他的心。
他想叫他一声棉棉,捧着他的脸告诉他你这样很漂亮但是这样我很心疼,而不是端着骄矜的高姿态跟他说,k159号,你风骚浪荡狼狈无助样子很合我的心意,他明明知道夏棉期待救他的是会送祈祷他好运连绵的桂圆味的月亮的俞骁,而不是这个藏在面具之后的矫揉做作的陌生男人。
想说的有很多很多,可也许这24秒倒计时到尽头,它们就会从暂时不能倾吐的隐衷被一把火烧成永不见天日的秘密,随着焦臭与灰烬烂在俞骁消失的心里——他永远没机会说,夏棉也永远没机会知道了。
我以为我生为军人,牺牲和奉献是我的使命与光荣,我以为我虽然深深遗憾但从来毫无怨怼。
不是的,我总是在训练与工作到疲惫至极的深夜里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又浑浑噩噩地醒过来,一个人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游魂一样来来回回地飘来荡去,像是想要寻找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黑暗像沼泽,浓稠的液体紧紧包裹着我的身体,连每一个细小的毛孔都无法透气。
我总是找不到,我不知道我要找什么,但我总是找不到。
我将每一扇门每一扇窗都打开,黑暗充盈了每一个角落,似曾相识的每一个角落,陌生崭新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液体一般的黑暗,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木门转动时发出吱呀吱呀不堪重负般的声音,像极了我似乎不知何时曾听过的,来自你喉间压抑到令人窒息抓狂的呜咽低泣。
无数个夜里,循环往复。
寻寻觅觅,像是精神病人的刻板行为,我停不下来,也找不到能让我停下来的事物。
奇怪,我明明听到你的声音。
轻如试探的一声,尾调微微上扬,是你在叫我的名字。
我找不到记忆,也找不到你了。
这个在黑暗中隐隐乍现的念头,使我在梦游一般的时刻被一阵剧烈的痛苦与惶恐催醒,夜色浓稠鞭辟入骨,我总是揪着头皮跪倒在地,无法喘息。
我的心,它远比我自己知道我在悲伤,在怨恨,在崩溃。
它比我自己更清楚,你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原因。
它比我自己更明白,你在我曾预期过的千百种未来里,那是我想要成为我的缘由。
当你不见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曾从哪里来,又该去向何方。
我有一腔义气应当报效国家,我应慷慨无私不苟私情,我一遍遍告诉自己,像是自我催眠。
可我又见到了你,我无数个夜里找过的你重新出现在眼前,带着真真切切的伤痕与体温,我惶恐后怕又无法掩藏那一丝丝可悲可哀的窃喜。
我应该专业敬业,不该为你推翻已经部署过千百遍的计划临时变卦,可我如何骗得了我自己,你不是那个我唯一不想辜负的人。
回来,24秒如何够,24年都不够。
前世太空,来世太远,只有现在是真真切切的,我想和你一起长命百岁。
24秒的第17秒,俞骁终于抓住了夏棉。
火与高温燎伤了夏棉的一缕发,持续收紧的牙关将俞骁的唇刺破了,伸长的犬齿上滴滴答答落下猩红的鲜血来,坠在夏棉的脸上,溅开一朵朵殷红色。
潮湿的青苔气息隐隐渗出一丝似有若无的雪松香,像是某种压制出现了松动。
夏棉于纯然滚烫濒死的幻梦中被呛醒,滚滚烟雾浓烫得像是泡在烟囱里,单手环抱着他的人把他整个藏在怀里,艰难上移。
他听到战鼓般咚咚咚敲在他胸膛上的心跳,像海上起风时,惊涛拍岸。
浓烟挤占了所余不多的氧气,夏棉无法正常地喘息,也无法像俞骁那样做到长时间闭气,他怔怔地在令人泪流不止的滚滚浓烟中贴着俞骁的胸膛看了一会儿,虽然什么都看不清。意识再次渐渐抽丝剥茧般痛苦无比地剥离的时候,他被迫蜷缩在身前的手在仅能施展的空间里软绵绵地握了握俞骁的衣襟,像一个未能舒展完成的拥抱。
俞骁的动作未停,只是环抱夏棉的手臂勒得更紧更用力,这是他此时仅能给予的回应。
他的眼球与浑身的青筋都剧烈地暴突起来,模样像极了被吹到极限的气球,像是随时可能会嘭——!地一声炸开血浆迸溅,湿滑甜腥的液体从他被铁链勒紧的指缝和掌心源源不断地渗出来,血迹河流一样淌湿了他已被高温灼伤的手臂,发出滋滋滋宛如浇灭火炭般的声响。
还不能结束,吞咽不完的血沫从他咯吱作响几乎咬
碎的牙关滋滋冒出来,俞骁几乎是凭着这股信念在失明的黑暗与浓烟中前进上移。
被逼到极限的精神驱动身体迸发出可怕的爆发力,他蓄力过后破釜沉舟般地猝然发力,密不透风的烟雾终于霍然被撕裂开一大道口子,潮湿腥咸的海风卷着潮汐逐浪的声音呼啸而来。
耳鸣尖锐,警钟般持续高分贝作响,俞骁咳得满嘴是血,视野仍旧没有恢复明亮,却本能地抱着夏棉凌空180度转了一圈,将他完全护在自己怀里。
嘭——!海面上溅起高高的巨浪,他们带着火烧火燎的烟雾从百米高的烟囱塔楼坠落,簇拥而来的海浪如同坚硬无比的地面,俞骁的身体严严实实地护着夏棉,结结实实受了这如从高空坠楼般的悍然一击,剧烈的冲力之下震得他死死紧闭的唇角无可抑制地涌出大股的鲜血,血丝猩红的眼球片刻间溃散,像四散的蒲公英,只留下黑魆魆的一片虚无。
还不能结束。
我们还不能结束。
你们体验过濒死的感觉吗,割腕放血这种慢的不知道,但是快的那种方式的确会看见以前一些你甚至没记事的年龄发生的事,不过不会像黑执事里画的那样有走马灯,本章描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时刻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也别去试着体验